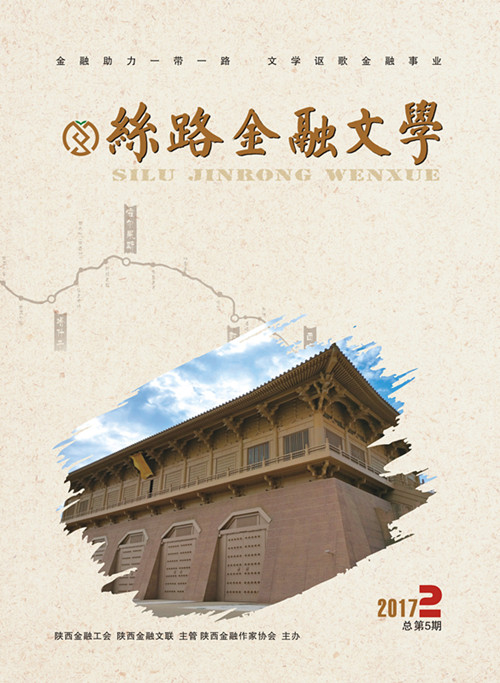冯唐曾在他的那本有趣的书《三十六大》中,第二十四则《大喜》里有过一个妙句“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春天刚涨起来的水,抽绿叶的树木,柔和的春风,也不及你的温柔!将一个春水、春林、春风的盛大春天的美,落在春花般的少女身上,有一种叫人神为之夺、目为之眩的美丽。这个站立在初生的春水、初盛的春林,与扑面不寒杨柳风之间的少女,定然是肤如玉烟、柔情似水的,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没有一个字形容“你”,然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真正的美,其实是无法形容的美。从西方的海伦到中国的罗敷,莫不如是。
女人是水做的,少女的脸庞,总是焕发出欲滴欲流的水嫩,仿佛一层细纱,一层淡淡的绒光,隐隐地透出珠宝的光芒。无论她五官美丽与否,那一种新鲜的青春光彩总会将旁人的眼睛照亮。岁月的大风吹过,衰老的最先征兆是那一层润泽水气的消失。十七八岁的肌肤是透明的,二十七八岁的肌肤是半透明的,再往后,便只是日趋黯淡与混浊。由如脂如乳的白嫩明净,变成泛灰的晦暗颜色,女人的花样年华就此走过了。即使有人精于保养,脸上就算是红光满面,也感觉比较凛冽,那层淡淡柔和的绒光,那一层神秘的肤如玉烟,早已消散不见了。浆果般的少女被命运的采摘。一点甜香,四溅在手,谁的唇齿间、指尖处,仍会依稀记取那一缕缭绕的余香?当年的她,与如今的她,其实是同一种植物,虽然在季节的循环中有所变化,但更重要的是,当年那个感叹“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的人,眼光已不再如水,一如既往地浇灌她,或许那是她曾如此滋润的原因?更甚至,她成为了一个生活在失望与疲惫之中的女人,东抓西抓,唠叨抱怨,一颗心被打磨得粗糙不堪,接近沦为一只求生的母性的兽,怎么可能与美丽有缘?
每到春天,总是感觉天地之间氤氲着一层润泽的水汽。春雨如织,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天是一个何等滋润的季节,而到了草木摇落的秋天,只有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枯裂干燥了。从童年到青春,是一个柔润发旺的进程,而青春既尽,急转戾燥干和。谁没有青春年少的时候,那些懵懂冒着傻气的言行,是嘀嗒在窗玻璃上的春雨珠子,尽管我们知道它们终将蒸发,无声无息消散在空气中,留不住抓不住,但蒸发之前的声响、滋润的触感,甚至冒出水气的味道,都让我们觉得这世上还好经历过,有你曾经在身边。抚摸初心,回顾来径,像一场春风,温润而柔美的吹到脸上,像一场春雨,慢慢就湿润了心。
春天的空气是湿润的,方便绿叶儿、嫩芽儿随时喝水;阳光是温和的,方便人们远眺近观秀色的时候,不用眯眼。叶儿、草儿、树儿、花儿都得天独厚,攒足了劲儿,比赛似地生长。一晃眼,就已经是花的海洋,漫山遍野,在春风里尽情妖娆着。晨雾似乎是被轻风融化在草间和花丛中,结起的晶莹露珠,滋润着细密的小草和散落的小花。阳光如水,物物清润静正,美得有情有意。而春江花月夜,明月悠悠然,独步中天,以一份银白洒遍无数屋瓦、窗扉、庭院,让人间千壑生烟,万物滋润。春天下起雨来,也是温文尔雅,不怒不狂、不横不躁,微微、悠悠、温温、和和、潇潇、洒洒,落在树木上,树木叶繁枝茂;洒在庄稼上,庄稼低头似饮酪。潮湿的雨后,一尘不染的欣喜无处不在。雨润径泥,草木植物像是蒙着一层薄薄的水汽,用手沿着花草轻轻一抹,便能搜集一掬雨水捧在手心,清清亮亮的。何时无雨,何处无水,可是只有在春天,你才格外地感觉到,与世界的关系是爱抚的关系,温润无比。
我喜欢现在,迎面扑来满满的湿润的春天的味道。蓝天之下,有清风掠过,尽情享受每一缕阳光的温暖,感受每一滴雨露的滋润,让相惜的暖意在风和日丽中增长,再一次感受与世界最初的爱恋。

一个流连于博物馆的人
我是个特别喜欢流连于博物馆的人,因为文物象征着消逝的旧时代,再浩大的城——包括那些繁华的街市,苍老的城墙,笨重的石像,耽美的错彩缕金,最后都会消逝无踪,只剩下劫余残灰的几件散断文物,携带着各自飘零的印记,日暮的苍凉和季节的深邃,在博物馆里无声展现消逝之美,展现曾属于自己的辉煌时代。当一切都要结束的时候,人类或许只能求助于艺术与器物这样的形式来自我祭奠,因为这是我们存在过的唯一证据。那些穿越了千年万年的人类手工制品,凝结着万物灵长的骄傲与谦卑,以及在时间维度上的某一节点的渺小感,曾在平和澹远的寂寞泥土中,默默守候了如许年,终于因缘际会来到我们的面前,被我们细细观看,被我们静静感知。走进博物馆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和哪件艺术品在哪个时空产生奇妙反应,这一切只有走进博物馆,才会知道。巨大玻璃柜中斑驳的陶器,生了绿锈的青铜,巧夺天工的玉器和精美绝伦的漆器,每一件物品似乎都具有一颗灵魂,争先恐后,窃窃私语,让你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让你得以了解比你生命更久远的事物。
走进博物馆,如同沉浮于一条凝聚着词与物、光与影的历史之河,有时会感到一阵恍惚,对于河流所代表的岁月无常,有时我甚至不敢去多想。某些无法言喻的时刻,急管哀弦的,时光卷轴徐徐展开,灯光有点动动荡荡的,似乎看到古中国了,悠久、缓慢、雅致、多情。昏昏黄黄中浮现了枯藤老树昏鸦,浮现了红酥手黄藤酒,浮现了蓝田日暖玉生烟。
几乎脸贴在博物馆的玻璃柜上,端详一件简静如璞玉的南宋官窑,眼前常会化出一片幻景。在那个千峰翠色的春天,细雨中一群身披蓑衣的窑工,表情缄默地燃香祭完窑神。坐定,喝一口酽酽的茶,捧起素胎上釉。在炉口看火焰的变化,根据变化迅速地选择时机加柴或封火。他们都是千里挑一的高手,把釉面的天然开片作为追求的境界。各种冰裂鳝血纹、蟹爪纹、梅花纹、流水纹、鱼子纹、百圾碎,在月白、粉青、米黄、油灰的釉面上,成之偶然、纵横交错,极不规则又在规则之中。窑工们凭着经验,静候神秘的窑变,“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从釉色到开片,都非主观意志能够左右。他们用墨汁、茶叶汤等高丹宁含量的液汁,巧妙施抹使裂缝着色,使之与“紫口铁足”匹配,染出一种“金丝银线”的天然意趣。只见春风杨柳中,一炉新瓷开窑了。窑场上一片肃穆。临窑督造的修内司官员,小心地捧起瓷器细细查看。如冰似玉无疵点的选入宫中,供皇上享用。稍有缺陷的,当场摔碎,清脆的碎裂声回响在那个已一去不返的春天。
我们都是人生场景中的过客,这段场景走来了一些人,那段场景又走失了一些人。当年宫中美人把玩的一只秀净的鹅颈瓶,如今,成为我眼中博物馆玻璃柜内神秘的时光之瓶。王朝更迭,江山易主,世事山河都变迁,只有这只剔透玲珑的南宋官窑鹅颈瓶,走过了山重水复的流年,笑看这风尘起落的人间。而那些沦落为白骨的占有者,最终没有带走一粒尘埃。端详这样一只晶莹润泽、丝绸光泽、美玉质感的宋瓷瓶,仿佛听到一缕琴音幽幽地响起来,奈何每一个音都是滑向消逝的,有来由唤醒的记忆没来由地去了,怅惘那“记忆”来自何方,分明只是一种虚空处的想象。在刹那的穿越中,关山的月色不老,我是一个彻夜远行的过客。
记得有一个博物馆大门上,有这样一句题词:“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存在,这个民族就存在着。”这句话,值得全人类铭记。当喧哗躁动之后,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形态留存下来。而一个民族所拥有的自我认定的历史凭证,才是这个民族得以延续,并满怀自信走向未来的根基与力量之源。
一代又一代人类,站在时间的前面,你望我,我望你,最后消逝在时间里,伸手去捉,是泡沫的空气。所以,我愿意走到存放记忆的博物馆里,那其中仿佛有一支珍贵而温馨的芦笛,它时常给我吹奏着往日那些欢娱和惆怅;时常发出怀念和遐思的声音,在岁月笛孔里潜流过一滴滴那消逝了的生活情景和泡沫。生命就是一次远足与体验,我们每个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不管时光如何汩汩滔滔,一个人的声音和足迹,器物和服饰,手作和文字,如果能被另一个人深深的怀念和铭记,这就是永恒。

黎 荔,女,北京大学文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西安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办公室副主任,崇实书院学业总指导,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有重要影响的人文系列讲座《学而讲坛》的创始人和负责人。主研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艺术美学、中外艺术史、视觉素养与媒介素养、文化产业、创意策划。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和参编教材18种。
[责任编辑:云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