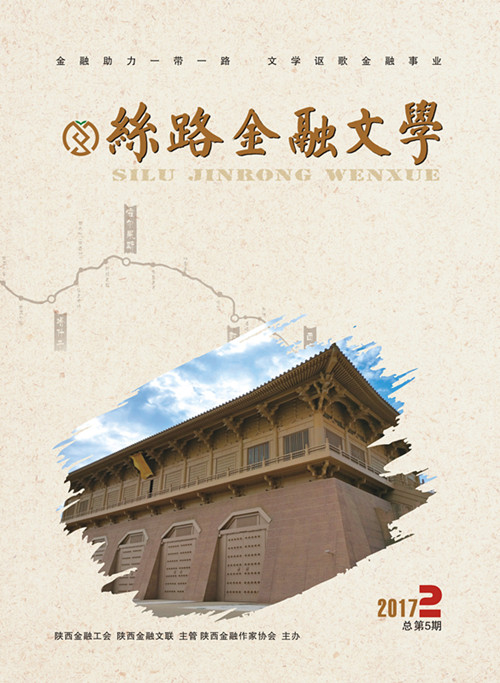2013年中秋节那天,母亲突然走了, 让我思绪处于极度悲痛之中。一提起母亲,我的泪水在眼窝里打转转,瞬即模糊眼窝。母亲就像我心中灯塔,她突然走了,让我站在原地,迷茫地想着、望着……
母亲身体一直康健,家里里里外外忙个不停。在2013年正月初,突然因肚子疼痛不忍,经多方医院确诊患有腺癌到晚期。这一事情重重压在我的心口,不能喘息。奔波于多家医院,得到医治最佳方案只有实施手术。无奈,手术过后,加速病情发作程度,医生劝告回家好好伺候,最多熬不过夏天。
那是在医院里,母亲一看,手术做了,催促我送她老回家唠叨说,病好了,出来多日家里猪鸡喂得怎么样,麦子快要收了,憋得慌,快回去儿啊。在一连串家务记事理由中,我执拗不过,送回到小县城。医生说,你手术体力未能恢复不能活动,要在县城医院疗养一段日子,才能回家。母亲听从医生嘱咐,为了快点回家,定下心在医院接受治疗。母亲躺在病床上,听着夏天知了分贝强弱起伏,身体毒素浸袭着各个器官,不时紊乱她的情愫,夜夜烦操,夜夜剧痛,看着满头流汗,身体扭曲形状的母亲,我的眼泪只能背过她无奈地刷刷流下。为了减轻她的疼痛,全家人采取一致口径,不能让她知道病变的发展,安慰她的办法讲讲在在农村勤俭持家片段,一段时间疼痛难忍,我反驳地说,你这叫啥病,看你在家里,饭也顾不上吃,坐在潮湿包谷竿中,一天苞完6亩玉米,晚间肚子疼痛炕上翻滚,那才叫病哩。母亲听到我们说这些话时,压低疼痛声音,额头上渗出汗水,抿着嘴笑着说,娃啊,农活要抢时间啊。母亲病情发作大都在晚间凌晨二点之五点钟,病房人多大声不能痛哭,她就低着头,卧在床上捂着被子无声流泪。这种场面让人看见比大声痛哭还难受。一月两月不见好,母亲在疼痛过后,唠叨似的不停地说,我得啥病啊,手术做了咋还不好,快些好哇,家里还得我照看啊。我支吾说些挨不上边的原因,您年轻时候肠颈连留下的后遗症,不碍事,住上一阵子医院,吃上一段药好了就可回农村干活了。
长长的夏夜终久是熬过去了。初秋早晨,我看到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医生反复确诊后,我用小车将母亲送回村里。村中四邻八舍知道母亲回来了,围着母亲炕头拉开了家常……
母亲在我们这个家中,虽然手中不管钱,但她说话分量很重。起早贪黑、辛勤劳作,过度的劳累脸上布满了皱纹,但结实的身板,急急火火帮人所难,在村中没有人比得上。在村里村外威望很高,人见人爱,总有说不完的感谢话。
母亲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从未跟邻居红过脸。母亲心地善良,特别喜欢帮助有难的人。一次有个陌生人路过我家门口,忽然发病,晕倒在地,口吐白沫,嘴里还不断发出奇怪的声音。母亲见状,用她当赤脚医生经验判断此人得了“羊儿疯病”。立即从家里拿来板凳,将他扶起,又是送糖开水又给他煨稀饭。病人缓过来后万分感谢。临走时母亲一再叮嘱“以后千万不要一个人单独出门,病倒了咋个办?”过去,有很多现在已经消失的行业。比如补锅的、修竹椅子的。母亲经常做“蚀本生意”。有个补锅工匠为我村补锅,向母亲要一口水喝,干了一天都没有吃饭了。母亲说这怎么行呢,挑这么沉的担子走街串巷。母亲给他煮了一大碗面条,加了很多猪油,比我们吃面条加的猪油还多。锅补好后,那工匠死活不肯收工钱,说“我的工钱还不够你的面钱。”母亲坚持要给,说出门挣钱也不容易付钱是天经地义,以后我走到你家门口你煮一碗面条给我吃不就得了。”那补锅匠鞠躬致谢,说:“大姐,你是在积大德啊。”
据母亲讲,在她记忆中,外婆侍候一大家老小,忙不过来,就留下她帮忙烧火做饭,等收拾完,再去上课,时间已经过了一大半,所以一个学期没有上过一个完整课时,断断续续上完了初小。由于我家人多劳少,爷爷又年老多病,生话的艰辛不言而喻。外婆动员她不要上学了,所以辍学就轮到她头上了。尽管如此,母亲还是不屈不挠的地跟命运抗争。擦干眼泪,女大当嫁,承担着新的家庭和生活的重担。
那个记工分吃饭的时代,家里没有男劳力别人是看不起的。母亲承担着抚养老人教育子女重任外,还起早贪黑,不误农时随同队长吆喝,锄地割草。为了多挣点工分,在我记事年代里,常常看见母亲因照看我的爷爷以及料理我们姊妹四个生活,误了时点出工,被队长喷血似的咒骂,让母亲背过人偷偷哭过。更为气愤的是分配男人不能忍受重活,母亲无悔干完到晚,记功分的时候,队长一句话,十分工分,记账簿上记载着三分工,就这还咬牙铁齿嘲笑说,男人都死完了,干了个啥球,记上三分就不错了,母亲听后要犯嘴,大队饲养室只有母亲一人辩护,其他家里无劳力女人家默不作声,一边看笑话,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公道话,急得母亲抹着眼泪回家,把我们兄弟每人抽了巴掌。在这记功分分粮的岁月里,十个劳动日等于10斤粮的分量。母亲当然急着挣。记得那是我在中学上学,看到母亲一人为了挣工分,将南岭十亩玉米地承揽下来,早上带着干馍,一直干到月亮出山,人还在地里,十亩长地头,靠着一人手包肩扛将玉米转运地头过斤两,可生产队长一看天都黑了,人走了,母亲大汗淋淋跑到100多米地头,好话多说,总算和会计过了秤。会计一边过秤一边蛮不在乎样子,10亩地包谷,从早忙到天黑,总斤两不及邻邦8亩地斤两,母亲质疑不准,队长黑着脸说,就这么多你还讹人不成,会计收工回家。看着一天收获还来工分和邻邦八亩地包谷斤两一样多,让母亲能说啥好,急的扯着会计衣角重新记账,母亲执拗不过,拖着一天没有喝一口汤水疲惫身子,摇摇晃晃回家了,回家一头倒在炕上,二天没吃没喝,邻居四妈过来开导说,不要争高低了,能挣多少算多少。这件事母亲一直纠结在心里。大约过了一年多还了会计,总算说出心里话,队长看到这么多包谷,少说折算工分也有50分,他们一天跑这边地头,跑那边地头,天黑也没有挣到20个工分日,看到母亲如此收入,便大打折扣,将其中1000斤两包谷算计到他们名下,事后分粮也能多分20斤。母亲听到后,微微一笑说,我早就知道他们做了手脚了。
上个世纪大跃进年代,我家是那个村子里生活最为困难的一家,父亲在外地教书很少回来,就算回来呆上一半天,根本帮不上什么忙,家里除了母亲参加队里的劳动能挣些工分外,几乎没有收入的来源,日子过的异常艰难。
在那个特别贫困的年代,母亲用那坚强的臂膀为一家老小扛起了生活的希望。地里的庄稼,家里的油盐酱醋,都是母亲一手操持着。母亲很能干,生产队里,正劳力一天挣十个工分,妇女一般五分或六分,我母亲被评为七分;正劳力的男人每年挣三千工分左右,母亲能挣一千八百多工分,再养上一头猪,积攒五十架子车青草肥,合起来也能在三千工分,一年下来,加上父亲二十多元的工资,勉力维持全家的生活。到年底若能略有结余,过年时我们弟兄几个还能添件粗布新衣或新鞋袜。
在我们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生活再穷再难,作为正劳力的父亲和爷爷必须吃“小灶”。家里有点细粮,正劳力吃,我们吃粗的;有点荤的,父亲、爷爷吃,我们吃素的。母亲对长辈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时发生的一件事。那天傍晚放学我第一个回家,先到院子里抱了一些柴草放到灶下,然后去写作业。我和母亲有个心照不宣的约定,只要放学回来写好作业后,母亲放工回来,灶上做饭,我就拉着那个沉重的风匣烧火,成了一个小小的“火头军”。我刚把作业写完,母亲便匆匆忙忙放工回来,放下农具,草草地洗了把手,就吩咐我烧火,然后进了里屋。
当母亲从里屋出来时,突然朝我吼起来:“你在家干什么事了?”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愣了一下。母亲见我不答,又严厉地问:“你爷爷的粑粑(玉米饼子)让你偷吃了吗?!”
我知道里屋的小筐里放的是男劳的干粮。母亲平日会烙一些饼或者做一些粑粑放起来,热一热就是有劳力人的一顿饭了。这份干粮我是不敢动的。
“我没有偷吃。”我老实答。“你还犟嘴!”母亲揪着我耳朵从灶下把我拉起来,朝我屁股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没有就是没有,你赖人。”我不服气地说。“就你一个人在家,不是你,那让狼叼去啦?”我低着头,委屈的泪水在眼圈里打转转。母亲知道父亲的干粮也不多,少了就要吃不饱,嘴里念叨着:“这可怎么办呀……”便把我撇在一边,急急忙忙地走了。一会儿母亲捧着一小瓢玉米面回来,我知道这是向邻居家借的。
“快烧火。”母亲生硬地命令。我在灶下深深地低着头,掉下委屈的眼泪,我受伤的心里一直不服。晚饭后,我提着小马灯,偷偷地进到里屋,四周查看,在微弱的灯光下,突然发现,在墙旮旯里有老鼠洞,边上有块黄灿灿的东西,我仔细一看是半块粑粑。我喜出望外地拿起来,急急忙忙跑到西屋母亲眼前。
“妈妈找到了,找到了!”“什么找到了?”母亲不解地问。“粑粑找到了。”我把半块粑粑捧到母亲眼前,母亲一怔:“在哪找到的?”“在老鼠洞边上。”
那一刻,母亲像一尊雕塑。
许久,她猛然把我紧紧抱在怀里:“该死的老鼠呀,真该死……冤枉了,冤枉……”母亲用那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妈错了,妈冤枉了你。”我抬头仰视着老母亲,她紧闭双唇,呆滞的目光停留在半空,混浊的泪水从母亲的脸庞上缓缓流了下来,滚烫的泪滴砸在我的脸上。我也哭了。那一刻,我看到了母亲眼神里的内疚与不安,听到了母亲心脏跳动的激烈忐忑,感受到母亲躯体的瑟瑟颤抖,那一刻,许久许久……
在艰难日子生活的母亲,穿着也极为朴素,很少见她添置衣服,一年四季就那两件衣服,仿佛从不离身。春夏总是那件深灰色连襟罩衣,而春秋两季的衣服则几乎是那件深藏青色的夹层罩衣,而冬天则穿着宋飞老爷邮递回来旧衣服改制的棉衣,每当我们问起母亲,母亲总会说,不出门成天围着锅台转,穿新的干啥。母亲从来不知为自己着想,也从来没有想着在自己身上花那份闲工夫。每到夜晚,母亲把厨房收拾完毕后,便坐在炕上,放好一堆衣服,然后就着油灯缝缝补补,几乎天天如此,夜夜如此,几个孩子,正是磨衣服的年纪,穿上破了,破了又补,母亲穿针引线不过多少衣服,我无法记清。只知道,自己一觉醒来,屋子里的灯还亮着,牛皮纸糊的的窗户上映着佝偻着的身躯,从来没问过母亲困不困,也没问过母亲累不累,那时候,无知单纯的我们是这般不晓事。
母亲说,她结婚后的几年里,村里也穷,家里穷的一年四季没有啥吃的。家里连个住处都没有,家里只留下两间破烂不堪土窑洞。一个星期天我和弟弟睡在一间土窑洞里,半夜一间土窑洞突然倒塌了,哭声惊动了邻家,母亲以为我们几个全完了,于是喊来村上,扒开倒塌的半间房屋,救出了我和弟弟。从这以后母亲下决心要盖房,那是家里吃的问题上顿不接下顿,那还有力扶盖房子哩。这事一直压在母亲长达20年,到八十年代初期搬出土窑洞,实现了她心里愿望。
母亲是一个重感情、重名节。母亲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人活脸树活皮”。无论村里红白喜事请客送礼,母亲从来都做得很大方,生怕别人说自己小气。一次家里好难得吃上一次饺子,刚好来了一位客人。母亲要我们等客人吃了我们再吃。她不断催我们给客人添饺子,结果饺子我们只尝了一点味道。母亲安慰我们说:“人家好难得来一次,招呼一下应该的,今天你们没有吃好以后妈妈有空再给你们做。”母亲一般不向别人借钱,一旦借了别人的钱,母亲就难以入眠。我读二年级的时候,家里一时确实拿不出学费。一个姓周的老师,也是我们邻村,我问她学费能不能缓缴。她反问我:“你去问你妈,她给我送煤我能不能缓给?”我极委屈地将原话告诉母亲。母亲只说了一句:“不同意算了,我去借!”这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母亲借钱,我知道母亲今天又会彻夜难眠。我5岁那年,不幸得了贫血症,不缴入院费医院不收治。母亲毅然将大爷送给她的手表卖了,那是她唯一的饰物。
母亲只有念了初小,没有更多地文化,说不出大道理,但她教育我们从小就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正值的人,不干偷鸡摸狗的事。她还用自己特有方式,不时对我的行为进行检验。一次母亲洗头,称自己手湿不方便,叫我将她裤兜里的钱掏出来。我看见有几个角票,还有不少硬币,难免心里痒舒舒的。几次想动邪念,毕竟胆子小没越雷池。事后我才知道,母亲兜里的钱她事先清点过,在有意考验我。从此以后,我牢牢记住了“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如果我在原则问题上做错了事,母亲对我惩罚很严厉,绝不手软。一次我和同学到公社影剧院“混票”,母亲知道后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几天以后屁股上的鞭子血印不散。母亲没有读过很多书,却经常教育我怎样做人。有一次,我从邻居家的鸡窝里捡了个蛋回来,母亲知道后,告诉我饿死都不能为盗,还亲自带着我把蛋还给了邻居。
母亲笑着说,小时候我三弟让她遭了不少罪。在三岁时,得了一种叫“百日咳的病,在最为严重的时候,上吐下泻,吐完了又哭,常常一晚上地折腾。到后来母亲把他送到县医院时,当时医生说,多半是治愈不好,不接收三弟。没有法子,只好带回,听说村远外一位老人有一个土方子,抱着试试看心情,捣鼓成草药丸子,吃了三天,竟然奇迹般的好了……母亲说这些时,没有流泪,只是眼眸里突然亮了许多,我常常是不愿看她,反尔笑笑。
有一年大爷从西安邮寄20元钱,大概也就是我四五岁的时候,母亲把我背到公社去取钱,可是才走出邮电局,就发现钱不见了……我不知道她当时是怎样走回到十来里外的家的,不过,母亲说她为这事儿难受了半年,不知掉了多少眼泪,没有经历过时代变迁的人,是根本不知道七十年代二十元钱是多么重量的,尤其在农村。母亲没有把钱被扒了是告诉父亲,她说她后来在地里四处挖刨,终于把那个天大的空缺补回来了,每次提起这件事,母亲总是感概万千,有时也认真地说,“要不是把你背上,不方便,就不会被扒了,心酸啊!”
母亲说,生二弟时,是最为穷困潦倒的时候。母亲吃着麦糠度过那最困难的日子,母亲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因为月子没有自身照顾身子才落下一生的病疾。因此,每当说起这些往事,她总是泪眼汪汪往下流,我知道这是母亲用自己性命换来的,如果没有母亲的爱,三弟那时是活不了的,因此三弟特别感激母亲,因此在母亲病重期间三弟细心照料母亲,打工回来后总是先去母亲那里看看,问问母亲的身体情况才回家,母亲住院,化疗透析两个弟弟忙前忙后在操心,我的妹妹围着母亲送吃送喝精心照看。在医院住久,仍然不见病情好转,我想回老家。我答应了母亲的愿望,母亲回到老家病情突然减轻了,我们都心里高兴起来,都放松了警惕,那天早上,她睡在土炕上静静地离开的,走时非常安详,象是熟睡过去,在她脸上没有一丝痛苦。
我知道,与其说母亲走的安详,倒不如说是母亲是带着未成实现夙愿无奈离开这个世界的。她想看到大孙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结婚了再走,想看到百里之外的打工老三小子——见一眼再走,但是病魔没有等待她老人家实现心愿,就匆匆地走了。
母亲没上过几年学,不识多少字,她一辈子也没有说过“人之初,性本善”之类深奥的句子,但她却用自己的行动,点点滴滴地向我们证明:对子女的爱,原来也有另一种方式,那就是无需张扬,不需要回报。
母亲走了,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母亲朴实的一生却值得尊敬,特别是母亲在我们最需要爱,最脆弱的时候,母亲用那无私的爱,用那双温暖的双手,是留给我们子女最珍贵的礼物,没有比这更为宝贵的了。
我曾想,如果没有母亲用她那瘦弱的双肩,支撑这个异常艰难的家庭,如果不是母亲坚持将我们送到学校读书,让我们开阔眼界,就不会有我们兄弟姐妹今天的幸福生活。可以说我们的一切是母亲给予的。有母亲的呵护,就没有我幸福、快乐的童年;没有母亲的勤劳,就没有今天拥有的一切。母亲,如果你还健在,我一定要好好孝敬您老人家;母亲,如果还有来生,我还要做您的女儿。
母亲走了,她的音容笑貌,时常岀现在我的脑海里、闯进我的梦里。母亲的坚强一直影响着我,让我有信心和勇气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有时想母亲了,自个安慰,母亲好像是在田间劳动去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儿欲养而亲不待”,面对一堆黄土,我只能把对母亲深深的思念,变成一串串晶莹的泪珠洒在母亲的坟头……
有诗赞母亲:寿越七旬睦邻精神令犹在,含笑九泉懿德嘉行永世存。珠泪成线天,香心化彩云,更用好花绣,风尚铭记载,倩影瑶池去,母亲天国安。

【作者简介】宋君翔,男,1965年4月生,陕西永寿人。供职于农业银行陕西咸阳分行。毕业于西北大学汉语言学专业。系陕西作家协会会员,陕西金融作家协会理事,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会员,洪厚甜导师工作室书法培训中心辅导员。
【本期责编:云鹤】